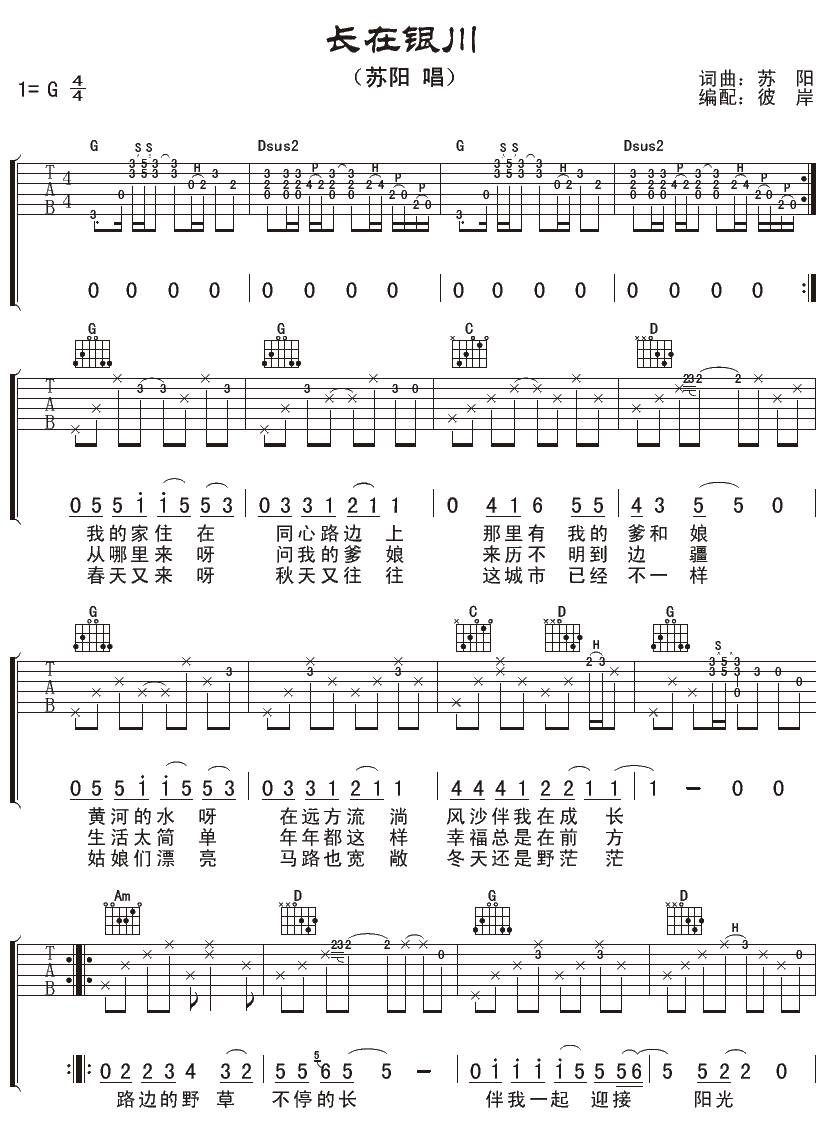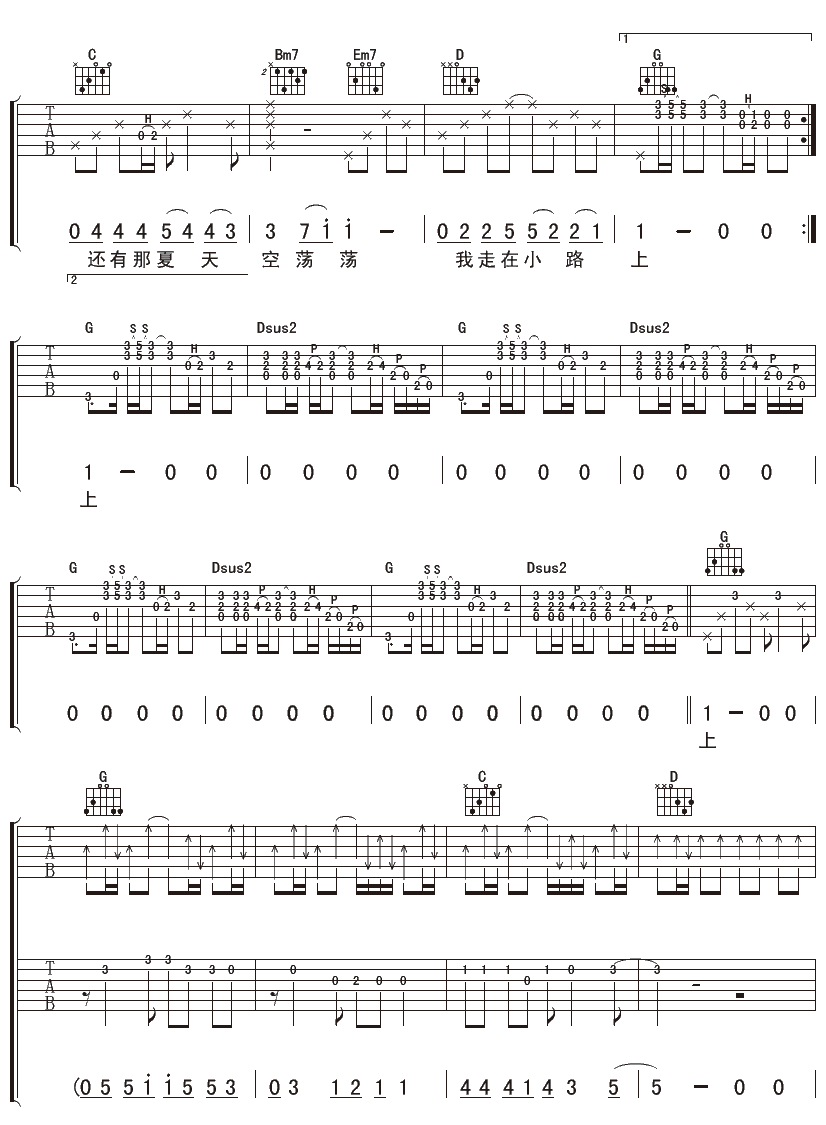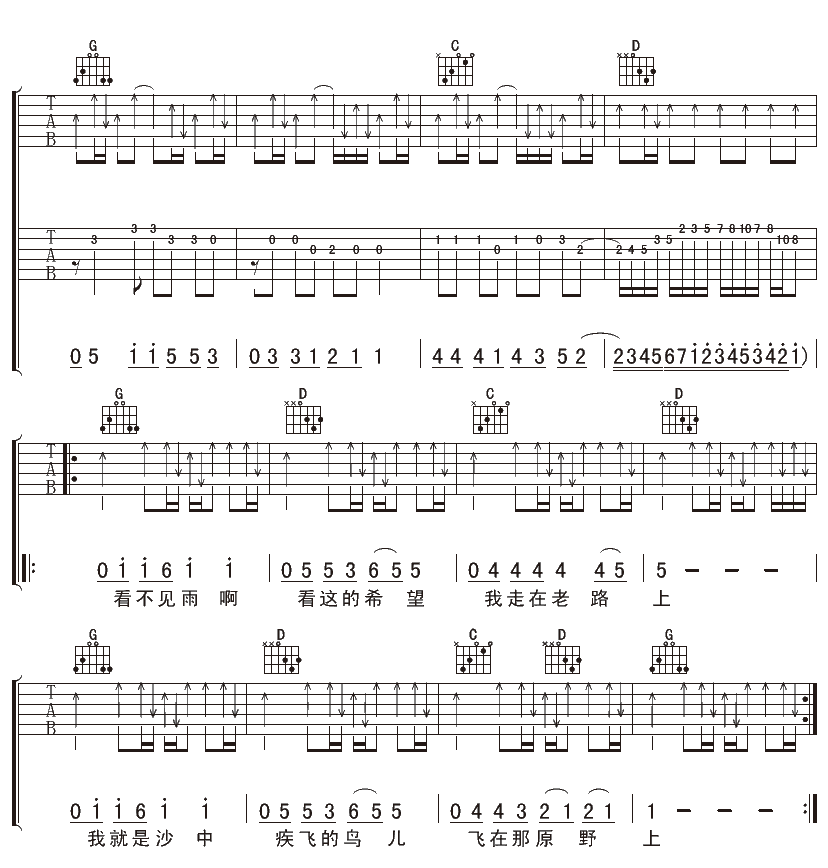《长在银川》以质朴的笔触勾勒出西北土地上顽强生长的生命图景,盐碱滩与黄河水构成矛盾而统一的生存底色。歌词中反复出现的沙枣树意象,既是干旱环境中坚韧的植物符号,也隐喻着世代与严酷自然对话的生存智慧。贺兰山岩画作为时空坐标,将个体记忆与远古文明悄然叠印,黄河水裹挟的泥沙在指缝流逝的细节,暗喻着无法截留的时光与乡愁。羊皮筏子与枸杞地的意象群,构建出既有地域辨识度又具普遍性的成长叙事,工业城市的灯光与旷野星空的并置,揭示现代与传统在塞上江南的微妙角力。歌词通过对西北风物的白描式书写,超越单纯的地域赞歌,触及更为本质的命题——在贫瘠与丰饶并存的土地上,生命如何以倔强的姿态完成自我塑造。沙暴中依然前行的身影,最终成为这片土地的精神图腾,那些被风沙打磨的温柔,恰恰构成对坚硬现实最诗意的反抗。全篇没有刻意渲染乡愁,却在黄河拐弯的弧度里,在沙枣花开的香气中,完成了对故土最深情的辨认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