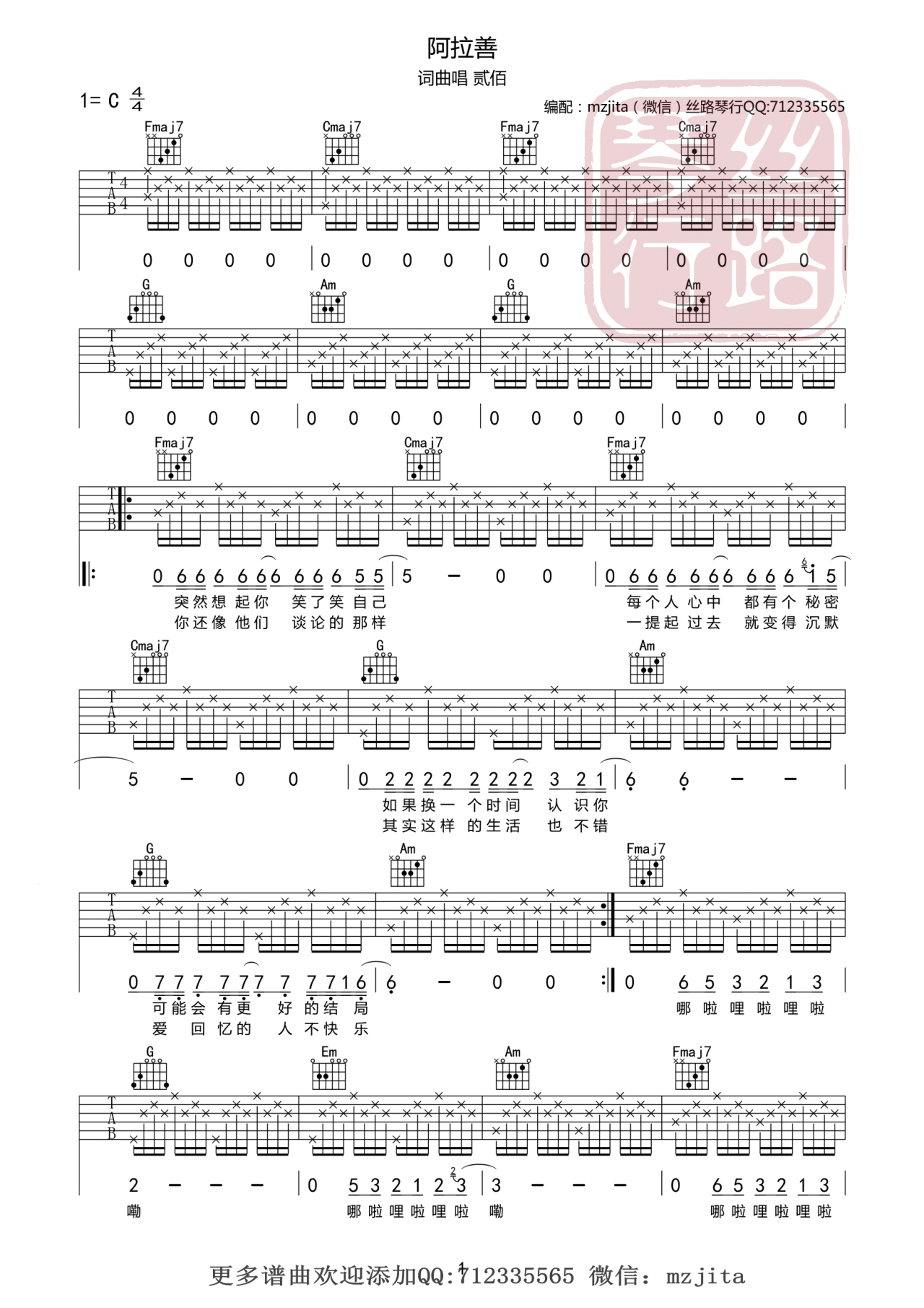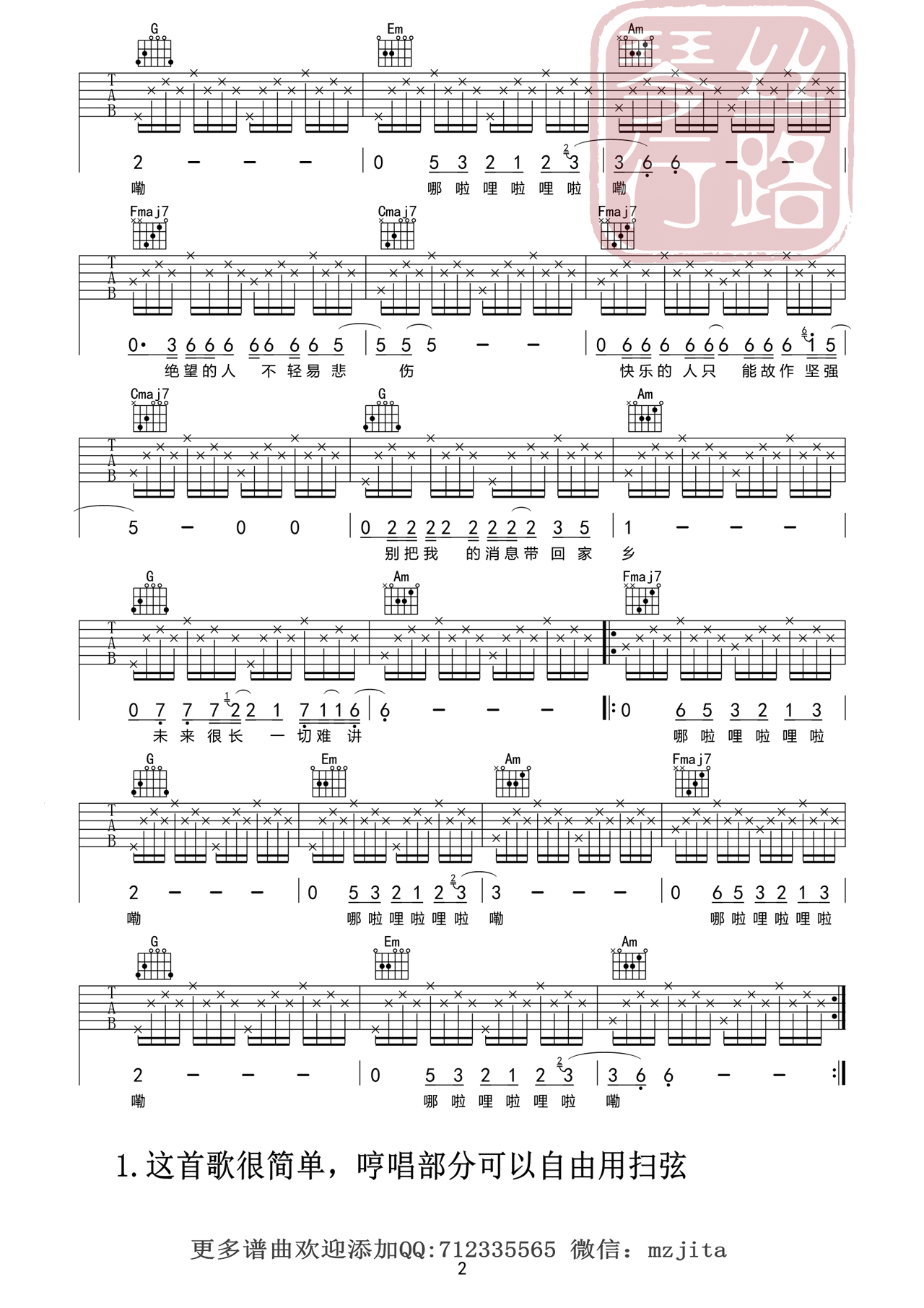《阿拉善》以苍茫的戈壁为意象载体,通过驼铃、落日、沙丘等具象元素构建出时空交错的叙事场域。歌词表层描绘大漠孤旅的苍凉图景,深层则隐喻现代人精神家园的荒芜化生存状态。胡杨林的三千年生死意象构成贯穿性的哲学注脚,既指向自然界的生命韧性,又暗合文明轮回的永恒命题。风蚀岩画作为历史符号的在场,与流浪者的当代足迹形成时空对话,揭示出人类始终在追寻与遗失间往复的宿命感。歌词中反复出现的"干涸河床"既是地理特征,更是情感荒漠的象征性表达,而沙暴中若隐若现的海市蜃楼,则巧妙解构了理想与现实的永恒悖论。马头琴的呜咽音色在文本中转化为集体无意识的情感密码,将个人孤独上升为族群记忆。全篇在生态叙事与人文沉思间保持微妙平衡,最终在"星光刺破夜幕"的意象中完成从绝望到救赎的审美跨越,暗示生命总能在最荒芜处找到存在的诗意证明。这种多重意蕴的叠加使作品超越地域限制,成为探讨人类普遍生存困境的现代寓言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