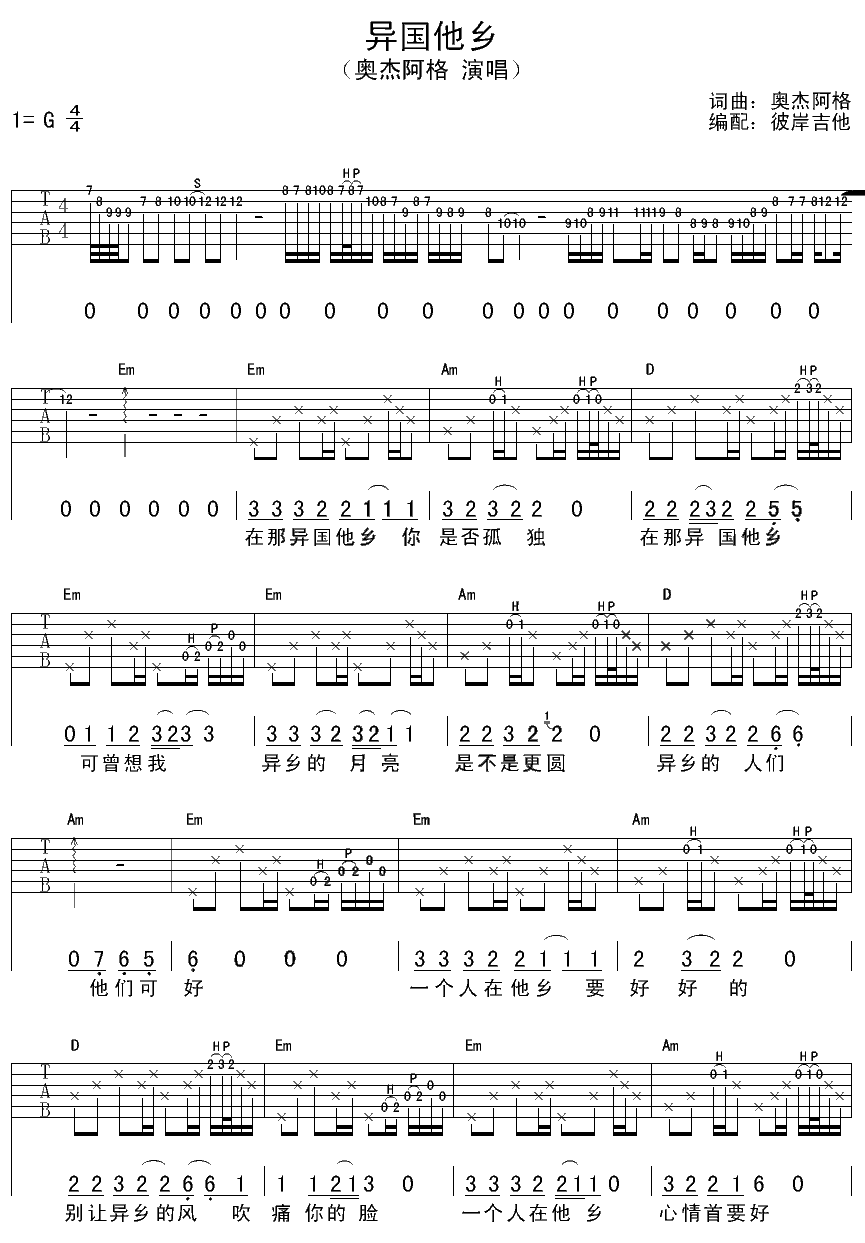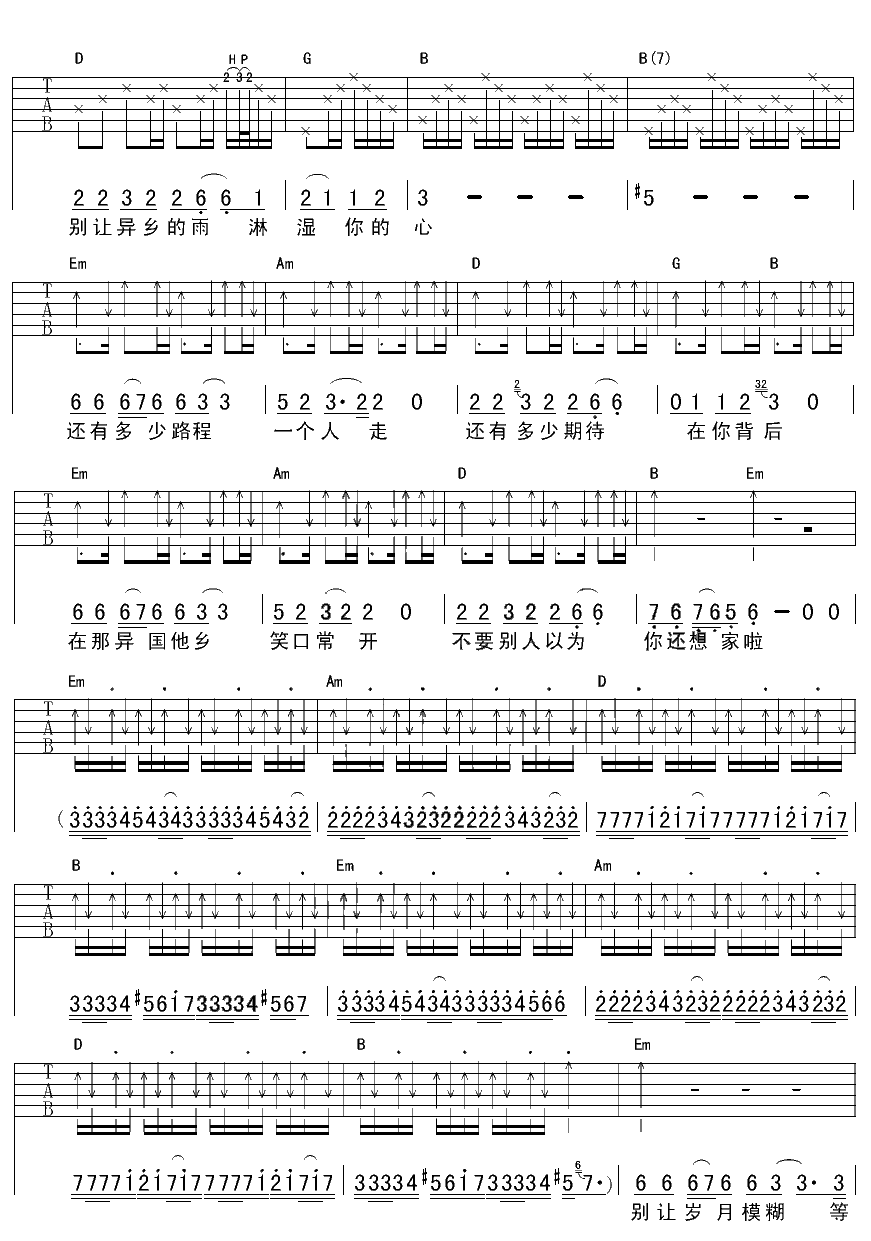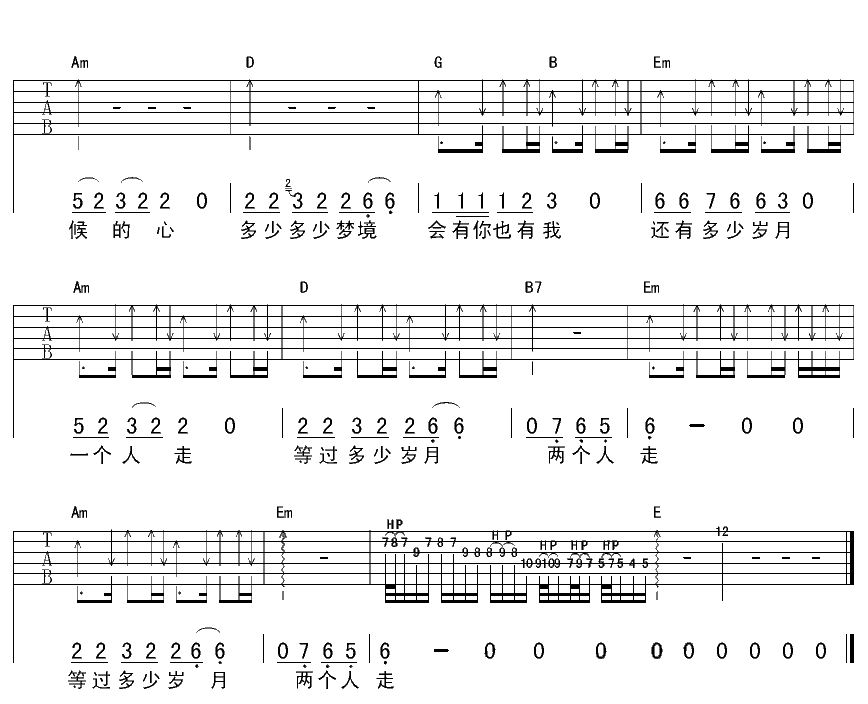《异国他乡》以漂泊者的双重视角构建叙事,既是对地理距离的丈量,更是对文化根脉的追索。歌词中反复出现的行李箱意象成为流动身份的隐喻,磨损的滚轮刻录着跨洋轨迹,而夹层里泛黄的照片则凝固了无法托运的乡愁。时差在此不仅是地理概念,更演变为情感异步的象征——故乡的炊烟与异国的霓虹永远隔着十二小时的月光。第二段主歌将语言困境具象化为"结结巴巴的春天",语法错误堆砌的围墙外,母语像野生藤蔓在梦境疯长。这种文化身份的撕裂感在副歌达到高潮,用"用咖啡代替早茶"的日常妥协,揭示移民群体隐秘的自我重构过程。桥段处突然插入的方言童谣构成全曲最残忍的笔触,传统调式与现代电子音效的碰撞,暴露出记忆修复的徒劳。最终歌词停留在"天气预报两个城市"的平行时空里,这种刻意未完成的结尾,恰恰映射了全球化时代移民的普遍困境——永远在抵达,永远在出发。全篇通过具象物件的诗意转化,完成对离散体验的拓扑学测绘,让听众在行李箱开合的瞬间,听见整个太平洋的叹息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