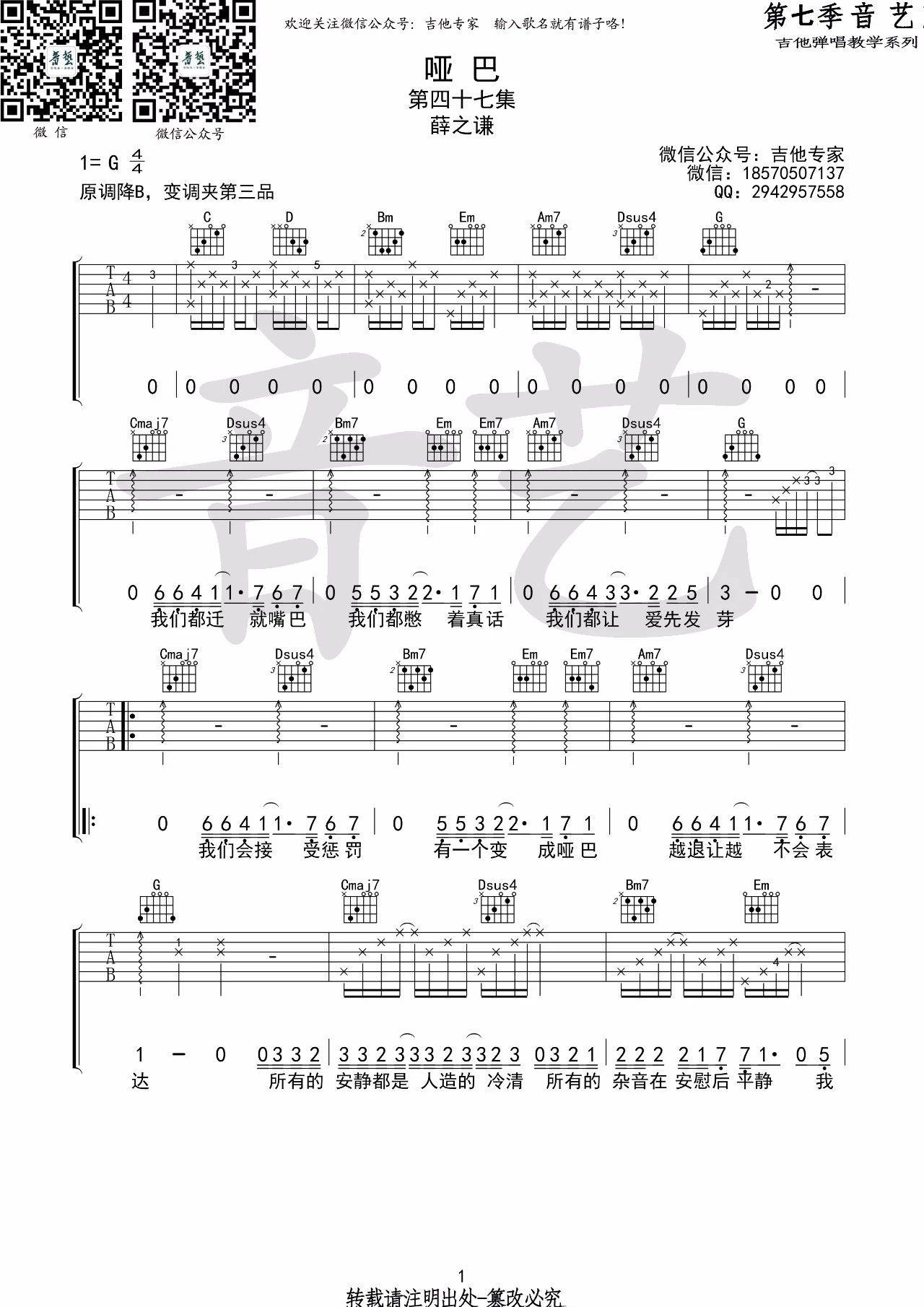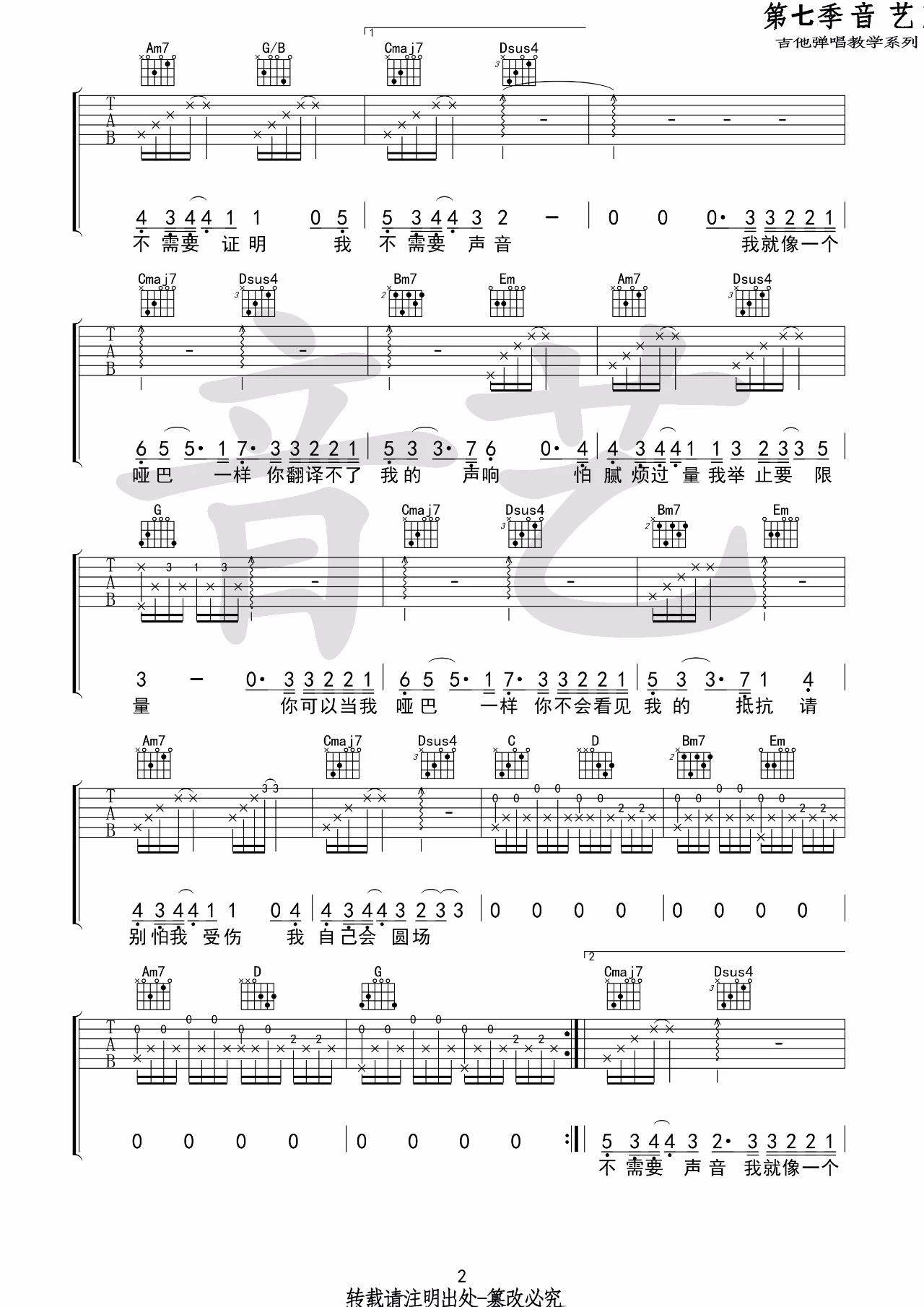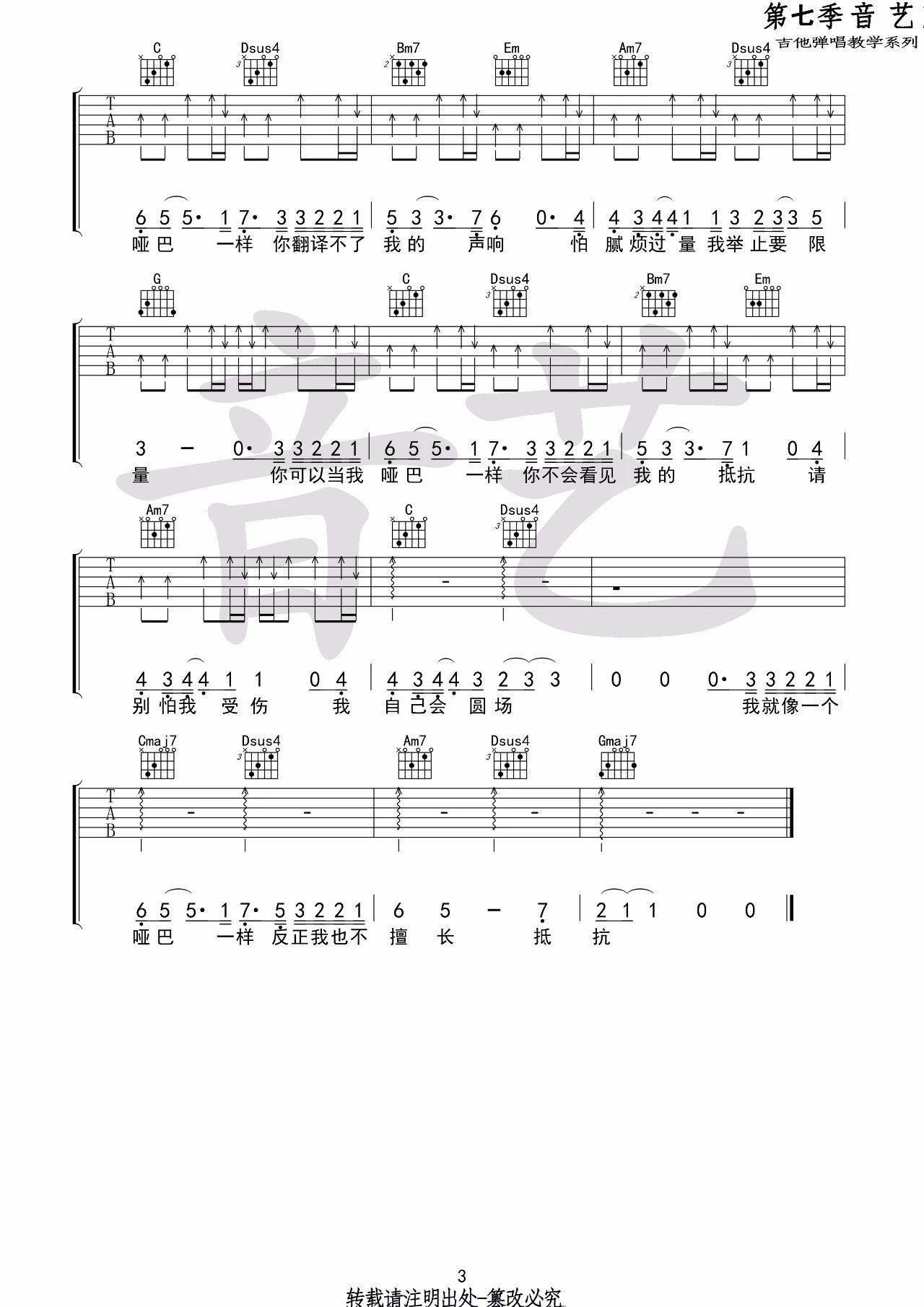《哑巴》以隐喻手法勾勒出失语状态下的心灵困境,借“哑”写尽现代人情感表达的滞涩与孤独。歌词中无声的呐喊与错位的对话,暗示着人际关系中难以逾越的沟通壁垒——当言语失去传递真心的功能,嘴唇开合便沦为徒具形式的表演。那些未能说出口的词语在胸腔堆积成礁石,既是个体被误解的痛楚,也是对喧嚣时代的沉默控诉。 歌词表层的“失声”实则是精神层面的喑哑,人们在数字化洪流中越是频繁发声,越可能失去深度表达的能力。道具般的语言、被曲解的眼神、僵化的笑容,共同构成一场盛大的集体性误读。而“哑巴”的处境反而成为某种清醒:当语言失效时,肢体蜷缩的阴影反而更接近真实的自我。这种悖论式表达揭示了存在主义的荒诞感——唯有放弃徒劳的言说,才能守护内心最后的完整。 最终作品指向一种超越言语的理解可能。在寂静的留白处,未说之言反而构建出更为辽阔的共鸣场域。就像黑暗中相触的指尖,失语者用另一种密码完成对世界的重新编码,那是在语言废墟之上建立的新型沟通范式,脆弱却真实。